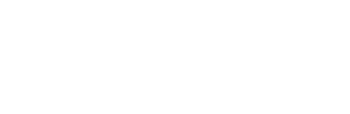無家者跟你想的不一樣!談無家者的宗教實作與認同 ft.黃克先【作伙來想社會Podcast EP1】
你是否曾在街頭上看過這樣一群人?他們露宿街頭、無家可居、天氣寒冷或颱風到來時,可能會需要政府單位或非營利團體的物資協助。
究竟臺灣的無家者是怎樣的一群人?而最常接觸他們的組織如教會、廟宇,乃至於非營利組織等,是怎麼看待這群人、如何與他們接觸的?為什麼過去媒體、學者會認為,無家者參加教會、陣頭等宗教活動,只是為了物質利益,而並非有「真實的」宗教?
本集來賓是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克先。黃克先老師多年來從事關於無家者的田野工作,與他們共同生活、探究無家者的日常、世界觀、困境,與面對各種社會壓力時的能動性。本集節目將帶領聽眾,討論常與無家者接觸的宗教團體、NGO組織對他們的看法、為何有時他們的「善意」反而造成對無家者的傷害。無家者自身又會如何主動的協商、反抗、回應社會加諸於他們的期待?並且,不同性別的無家者有什麼不同的處境、回應壓迫的方式?研究者在接觸無家者時,自身的性別等社會角色,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?

主持人|蔡博方(臺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、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)
來賓 |黃克先(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)
本集重點:
02:31 為何會選擇使用「無家者」這個名稱,而非「街友」或「遊民」?
05:27 接觸無家者好像很可怕?是如何進入無家者的研究田野的?
08:21 接觸無家者很有愛心?對一般聽眾而言,如何接觸無家者可能更恰當?
09:57 中介機構對無家者的看法?他們的「善意」反而可能傷害到無家者?
14:35 NGO與宗教團體有類似之處?無家者不符合他們期待的理想樣子會如何?
19:21 面對權威者的壓迫,無家者具有能動性嗎?為什麼無家者被認為沒有宗教?
25:14 一般對「宗教」的想像來自西方基督教,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定義方式?
32:09 為什麼女性無家者這麼少?女性的風雨,發生在有屋頂的地方。
35:49 研究者性別的影響:身為男性研究者,接觸女性無家者時的限制或近路。
39:06 Covid-19疫情下的無家者:跟SARS時期相比,臺灣社會有進步嗎?
於Firstory、Spotify、KKBOX、Apple Podcast等更多平台收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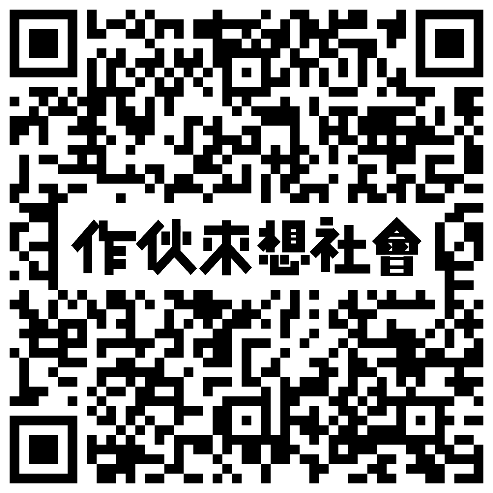
▌臺灣的無家者是怎樣的一群人?為何會選擇使用「無家者」這個名稱稱呼他們,而非也很常聽見的「街友」或「遊民」?
稱呼這群人的名稱其實非常多,在不同時代間一直轉換。如:清朝時叫他們「羅漢腳(Lô-hàn-kha)」;日治時期叫他們「浮浪者」──浮浪,好像漂浮在海上。到了國民黨來了以後,就叫他們「遊民」,就是把他們看做是散兵游勇、游離在社會當中的一群人。
後來有些人覺得遊民這個字眼帶有負面意涵,他們並不是那麼游離,也不是罪犯,不需要這樣稱呼他們。所以一些非營利組織提倡用「街友」這個字,但後來這個字眼也被認為有點矯情。其實你在街上看到這群人的時候,往往避之唯恐不及,根本不會把他當朋友,那你為什麼要稱呼他是街頭上的朋友?這種反差反而映襯出了社會的偽善。
所以就有些人提倡,我們就如實的用他跟一般人狀態差距最大的,居住空間的差異,來稱呼他們。就是他們無家、無可居,homeless,更精確地講應該叫unhouse,他們沒有一個家屋可以居住,所以就簡稱叫做無家者。
我覺得這樣的稱呼相較於其他幾個比較恰當。但不可否認,這樣的名稱還是有它的侷限。因為在漢人社會裡,「家」這個字帶有某些很特殊的情感上、象徵上的意涵。「無家」,我們會覺得:這些無家者怎麼會沒有家庭?好像特別的有問題,就會想說一定是拋家棄子等等。但事實上,他們並不是沒有家庭,他們與家人還是維持著一定的聯繫,而是無家、無可居。所以這樣的簡稱,有時也會造成一些誤會與隨之的污名。但相較於其他的名詞,它還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字,所以我就會用個字描述他們。
▌為何會進行對無家者的研究?
我其實跟一般人沒什麼太大差別,對於這群人既陌生,有時也會有點害怕,對他們有各式各樣負面的想像。但因為我剛好是讀社會系,社會學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,是跟社工併在一起的,所以我們會接觸到很多社會工作,但其實社會學與社工是非常不同。只是在當兵時,很多人、包括政府都會覺得我們是一樣的,所以我們就會一起服社會役的替代役。
因為這個機緣,我到了臺北市社會局,接觸到「遊民」業務,當時我也只是從書面上、法規上去了解他們。但你說要真的跟他們生活在一起,其實我也非常的害怕。那種害怕比較像是,很多讀社會學的人會有種社會學的政治正確想像──覺得他們之所以這麼可憐,絕對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因素,而是社會結構所帶來的。
我們會非常抽象的知道是社會結構導致他們如此,但也會覺得……可以的話不要與這群人在一起,會比較開心自在。會很害怕變得跟社工一樣,實際去接觸他們,或者是直接與他們有所互動。所以我當時只是對他們的生活世界有些好奇,但其實不覺得自己有能力真的對他們做民族誌──就是跟他們生活在一起、嘗試瞭解他們怎麼看待這個社會與他們周遭的事物。
後來是因為一步一步,跟服務無家者的NGO有一些互動、實際上真的能面對面的接觸到一些個別的無家者,透過與他們交談,他們說他們的過去、現在生活的困境,慢慢地,他們在我的腦海中,比較有具體的一個「人」的形象出現,到後來才真的踏入了無家者的民族誌研究。整個前前後後過了大概有十年吧。
▌如何接觸無家者可能更恰當?
很多人會很好奇要怎麼接觸這群人。是不是就直接坐下來跟他們聊天、問他們需要什麼?我其實並不建議這麼直接。因為其實無家者這個群體,有一些精神狀況的比例高於一般人,並不是所有無家者都是這樣,只是如果一下就太過於靠近……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相處、一些觀察,慢慢拉近距離。
很多人會覺得我很有愛心,才能跟他們這樣相處,但我其實要交代,這不是有沒有愛心的問題。通常很多時候,它會需要一些中介。譬如說我一開始透過一些非營利組織的中介,逐漸認識了比較多之後,才進入田野直接接觸他們,直接到公園中跟他們生活在一起。
如果是一般的聽眾……因為我常遇到高中生問我:應該如何幫助他們?怎麼接近他們?是不是直接去找他們就好?我其實都會建議,如果有長期跟他們接觸、服務他們的人中介,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。
▌中介團體其實是大部分社會大眾要接觸無家者很重要的方式,會影響人們對無家者的看法。這些團體對無家者的看法是什麼?這些看法可能有什麼問題?
我覺得社會中需要這些中介團體、公民社會做為橋樑。但也不應該只停留在此,因為這些中介的機構或組織,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,有它自己的agenda,它想要完成的事情,它有可能因為這樣,呈現出特定的關於這群社會弱勢的某種形象。所以即便透過這些NGO或宗教團體中介,最終我們還是要去直面無家者,直接去面對這些無家者,才能比較準確地掌握他們到底在想什麼、試圖怎麼做。
看過我這篇文章的人,應該看得出,我對宗教團體有很明顯的一些批判,這種批判並非否定他們在幫助無家者上的努力;而是說在幫助無家者的過程中,這些團體其實也帶入了這些團體自己本身的議程,它們想完成的事。而這些議程有時候對於它們幫助的對象而言,其實是一種傷害。那種傷害應該要被看到,社會學會給我們一副眼鏡,讓我們去省思這樣的東西:
不是有能力、有資源可以去幫助別人,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完全正確的。還是要站在對方的立場跟感受,來看待這整件事情。
誠如我剛才所言,重點還是要去直接面對無家者本身,把他當作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來理解、傾聽他的聲音跟需求。不可否認,某些我田野中看到的宗教團體確實是這麼做,所以並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,並非所有宗教團體幫助無家者的方式,都像我文章中所批判的這樣。只是確實有不少會有這樣的問題,可能傳教的目的走在前面;或是期待眼前的人要變成一個很理想的基督徒,若非如此,會覺得花在他身上的力氣跟資源都是白費,所以會用很直接跟強迫的方式,希望他變成這樣的基督徒。
在我的田野中,不只基督教,包括佛教或民間信仰也有這樣的傾向。其實回歸宗教的本質,不應強加自己的意志,或是自己以為好的東西在他人身上,而是要看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聯繫。或許你會有一些好的東西想與他分享,那可以,但方式要如何做需要再商榷。
▌有很多無家者未必非常工整、順暢的符合這些NGO或宗教團體的想像,會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。能否講幾個例子?
我的文章沒有提到NGO組織,但可以一起談一下。晚近一些NGO組織,跟宗教團體某個程度上是類似的,它會希望、想像人應該是具有某種樣子。比如說,過去很多服務無家者的都是在物質層面,但他會覺得其實人都有文化上的需求,有需要宣洩、表意,表達自己的意念。所以他們會做非常多的文化活動,如:一起來演戲、做木工等等。
有時觀察會發現,參與其中的無家者會覺得非常的納悶。他會覺得:我有時溫飽都成問題了,為什麼這個組織一直要我來做這些事?或許這些組織有好好說明、得到無家者的同意跟諒解。但也有一些是沒有的。你會看到很多無家者,平常就是在在工地做粗工,比較有男子氣概那種樣子,他要融入文化活動就產生一些困難。但融不進去的狀況底下,似乎又會有種潛在的指責,覺得他不重視自己的心靈陶癒。
文章中有提到基督教會的例子,也是類似的狀況。它會非常強調你在聚會時,必須要有一個好信徒的樣子。比如說非常認真的聽臺上的牧師講道,要能夠理解他講的聖經故事,跟裡面的一些道德訓斥;同時要把這些道德訓斥,轉化成自己行為上的改變,比如說不要抽菸、喝酒,比如說來聚會的時候要準時,然後聚會結束要一起幫忙打掃,諸如此類的道德表現。如果沒有做到,似乎就會被認為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,沒有認真在轉化自己。若是如此,那教會是不是要停止供給一些飯食或服務給你?會有類似這樣的狀況。
這個團體或是組織本身,想像一個人理想的狀態。當你沒有辦法符合,就有可能就會剝奪掉它原本所承諾應該給予你的服務。
▌有沒有哪些無家者,比較能符合這些團體的想像?
在我的田野中,確實有一群人可以很完美的嵌合到組織所設定的模式中。從性別的角度切入來看,特別是女性無家者容易做到這樣的轉化。她們可能因為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,長期被教導:社會對妳的角色有某些期待時,應該要去適應;或應該要在情緒上配合他人等等。 所以比較能去做到、不會去忤逆所謂的權威。這樣的狀況也是存在的,只是要分析的話,需要別的概念工具,我這篇文章中較沒有做到。
我的文章比較是著重在男性的無家者,他們特別因為性別社會化過程中、工作環境中,各方面都在強化他必須要去捍衛他的陽剛氣質。所以在宗教層面,他也會非常主張:我有我的尊嚴、我有我想像的所謂「耶穌是什麼樣子」,權威告訴我的不見得是真的。我會更積極的去把它做一些搓揉,跟我所信奉的,比如我比較尊崇、推崇的一些武俠、俠義價值,去做融合,所以就會出現我們文章中所看到的狀況。
▌面對權威者的壓迫舉動,無家者具有怎樣的主動性/能動性?
這也是我在文章中很希望強調的部分。過去不管是大眾媒體、宗教人士,或甚至是無家者自己本身的講述中,都不會去凸顯無家者的能動性。我在田野中常看見,無家者會去參與各種宗教活動,他們的言談中也有許多與宗教相關的情節。但從權威人士、學術文獻中所看到的,卻是「他們沒有宗教」,或是沒有「真實的」宗教,無家者的宗教面向經常被否定。這也是我問題意識的出發點:明明我在現實上看到這麼多宗教元素,但為何從文獻上卻看不到?從大眾媒體上,卻覺得無家者去教會、去參加這些廟宇活動,就只是為了賺錢、為了非常功利性的物質誘因,而非任何我們一般理解的宗教精神上的追求。這樣的出發點,讓我試圖去描繪出無家者的主動性。到底他們在這些過程中,有怎樣的宗教認識、為何這些東西消失不見了?是在怎樣的作用下,導致他們的宗教主動性不容易被看見?
▌無家者是如何被界定為「沒有宗教信仰」?他們又如何翻轉這個標籤?
不管是民間信仰、督教信仰,對於理想信徒都有某些設定。無家者在具體的情境中,往往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設定。
之所以無法符合宗教權威的設定,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為他們成長的過程。包括他們的身體,也就是,在他們的成長過程當中,身體被訓練展現出來的樣貌;或是在目前流浪的情境中,無家者有時候可能睡不飽、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吃得很營養,可能身體較易染上一些疾病。
在身體上、精神上,或無家者長期以來成長過程中,各種習癖的養成。使得他沒有辦法如很許多人般,在宗教情境中,能夠把自己展演成「理想的信徒」樣貌。例如:聚會的時候非常認真聽,像是好學生般做筆記;出陣頭的時候,用他們的語言講,就是非常的「媠氣( suí-khuì)」──展現非常有精神的樣子,舉著旗子、無須他人訓斥,就能整齊劃一的走在隊伍裡面,透過這種方式展現神明的神威也是在他們身上。
無家者因為各種外在因素,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狀態。因此,在宗教權威的眼中,就會覺得他們不是「好的信徒」,或是他們沒有做到「真實的信仰」應該反映出來的樣子,並因此否定無家者有宗教性,會認為他們只是因為物質,如:要賺到錢,或者來吃一頓,所以才來到這個地方。
我文章中的主要論點就是:雖然他們沒有辦法展演出宗教權威眼中理想的宗教,但他們依然有他們自己的宗教存在。他們有他們主動去形塑他們宗教信仰的能力。
▌到底什麼是「宗教」?說無家者沒有宗教信仰時,背後的預設是什麼?
一般對「宗教」一詞的想像,其實來自於西方基督宗教的原型,認為那就是典型的宗教。若以那樣的標準看無家者的狀態,很容易便會覺得他們沒有宗教,因為他們並不會積極、固定的參與宗教組織或制度性活動。
但在中國傳統,以至於臺灣民間信仰的脈絡中,「宗教」的指涉其實非常廣泛,它不僅只是(如西方宗教定義般)非常有制度、明確經典的才叫做宗教。因此我在文章中用了比較廣泛的界定方式定義「宗教」──做為一個人、一個個體,如何去連結自己的過去與未來,與自己當下的情境;並用不同於一般習以為常的邏輯去結合上述事物──都把它廣泛定義為可以是「宗教」。所以它不見得一定要符合西方基督宗教,跟超自然力量做交往才叫做宗教,它也可以有非常廣泛的操作範圍。
過去是因為在西方特定時期發展下,我們才會將宗教想像成僅有「那一種」,非常制度性、嚴謹的宗教。但若從古今中外來看待,其實能對宗教有更廣泛的界定。也因為將定義拓寬,才能看見許多過去被掌握知識、發言權的權威所排除的一些現象,它們其實也非常鮮活地散布在我們周遭。
▌所以,無家者面對宗教權威或其他社會權威的壓迫,能有所反抗嗎?
在現代宗教的情境下,宗教權威掌控信徒該如何生活的力量,其實已經越來越衰退了。在今天,做為一個信仰者,其實相較過去有更多的主動性,可以去協商到底宗教傳統的什麼對自己有幫助。
前面做過NGO與宗教團體的類比,非營利組織所試圖要跟無家者灌輸的那些東西,與宗教是類似的。反過來說,無家者不管面對非營利組織或宗教團體, 其實也都有這種協商的主動性存在。
同樣的,當主流社會試圖強加某些中產階級式的價值在無家者身上──不管透過政府法令、福利輸送,或是大眾媒體形象塑造;當我們把自以為的「應該如何活」的價值放到無家者身上時,他們一樣有反抗、協商,或是在這之中找到一條不喪失自己主體性,同時又能回應社會的道路。
這也是過去研究社會邊緣群體的社會科學文獻較容易忽略的。有時我們說他們被資本主義壓迫;有時我們說他們被政府、國家機器打壓,容易直接給他們一個「受害者的位置」,但其實邊緣群體在這個過程中,並非不知道外在力量對他們的箝制,而他們在意識到這些箝制的同時,也有一些策略與堅持。這是做為研究者、做為一個人去理解他們的時候,同時要看到的。
▌ 除了前述女性無家者較能順暢的嵌入宗教權威的故事腳本外,性別因素在無家者群體中,還有什麼值得關注之處?女性的風雨,發生在有屋頂的地方。
就統計數字而言,女性無家者的比例遠低於男性,大約是1:9,這種差異的原因很值得進一步思考。難道女性在經濟上、各種面相上遭遇的困難低於男性,所以較不易無家可歸嗎?
我的觀察是:女性在性別社會化過程中,被教導的往往是跟家庭綁在一起,如果失去家庭,好像會是非常可怕的事。這點與男性不太一樣。特別是勞工階級的一些男性,他會很強調「飄撇(phiau-phiat)」、或是很瀟灑、我自己能夠做到別人以為我不能的事。
但在女性的社會化過程中,就比較沒有強調這一塊,反而好像始終就是要依附著家庭,變成一個好媽媽、好女兒等等。因為這種思想上的束縛,可能讓女性對於「無家可歸」這件事覺得特別的可怕──確實,其實也是特別可怕,在人身安全方面的顧慮會比男性多。
因為如此,女性為了要有一個屋頂,願意去忍受很多東西,包刮家暴、不當對待、性騷擾等等的。所以這導致了女性在街頭上比較不容易被看到。但她們遭遇的悲傷的事,是發生在有屋頂的地方。
換言之,街頭上的女性無家者,可能也同樣遭受到這些她們所顧慮的事,導致她們的行為模式、生活習慣也與男性無家者不太一樣。譬如我在公園看到的女性無家者,很容易身邊會有一個,有點像是保護她的男伴。她非常習慣,一旦無家可歸,她會需要找個保護者,讓她在公園中比較不會被欺負、騷擾。
我在公園中也明顯看到,一旦有個新的女性無家者出現,會有很多所謂的「蒼蠅蚊仔(hôo-sîn、báng-á)」,過去跟她搭訕聊天,問她需不需要什麼幫忙。很多男性也會告訴她們:如果要找保護者,我這邊就有。所以他們很容易最後會變成一對一對couple。不同性別的社會化過程,會導致她/他們在成為無家者的路徑上不太一樣;而真的成為無家者時,生活習慣、策略也不太一樣。如剛才說過的,宗教場域的性別化差異。
▌研究者自己的性別對於接觸無家者、建立與被研究者關係有什麼影響?
不諱言,生理男性的身分對我的研究會產生一些限制──也不一定只是限制,有時也會帶來一些方便的近路。在接觸女性無家者時,我覺得相較於同為女性的研究者,我能夠瞭解的比較有限,這一點我必須承認。
我常常談一個例子:我做完田野後,有再做生命史的訪談,這時我已有意識到性別的差異是個重要因素,因此故意請了女性研究生當我助理,並請她去訪談。她訪了一個女性無家者,那個女性無家者才剛開頭講沒幾句話,就開始抱頭痛哭。我這個助理問她的問題只是請她講過去的生命經驗,並非明確要她講傷心事。但她馬上就像在懺悔般,說她很對不起她女兒,因為她很丟臉、從事性工作等等。
我當時聽到助理轉告這件事,我非常的驚訝。這位無家者其實我也認識,但我認識她這麼久的過程中,她從來沒跟我說過類似的這些事。我因此非常明顯的感受到,我們在相處上,同性與異性相處的模式,可能還是有些差異。當然也有可能因為我是男性,女性無家者會特別願意跟我說某些事情,這個狀況也是可能發生的,如有些女性無家者會跟我抱怨她們的男伴,或她對親密關係的想像。
我覺得做為一個研究者,反思自己在田野中的位置,以及與報導人之間的關係,是很重要的。
▌過去幾個月臺灣疫情情境下,無家者的處境有沒有什麼改變?如果聽眾希望更瞭解無家者的訊息,有沒有什麼推薦的資訊管道?
這是疫情剛好也是在萬華爆發,五月中時,也傳出很多「疑似」無家者染疫、帶著病毒到處亂跑的新聞報導,後來當然都證實並沒有。還是可以看到在某些特定的危難時期,這些都市邊緣,仍會承受比較多的污名與壓力。
但我也想特別提出:跟2003年SARS期間相比,臺灣社會確實有進步。在對待無家者的方式上確實有改變。
2003年當時,也是SARS在萬華地區爆發,當時的台北市長決定用非常鐵腕的方式,幾乎是半強迫地把台北市的遊民,全部集中到大直的一個國防部隸屬營區,把他們關在那邊。這樣的對待方式,在這次疫情中就沒有發現。這次疫情中,反倒能看見如高雄市,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作法,如政府買單讓他們著防疫旅館;臺北市也有如讓無家者優先施打疫苗等政策。會比較站在他們的需求思考,而非直接將他們定位為病毒帶原者。這是臺灣社會比較進步的地方。
這個進步其實是展現在非營利組織的健全上。2003年當時,除了政府的遊民社工,其實並沒有太多非營利組織在關注這件事;但現在在萬華地區,已經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協力網絡。有好幾個平常就有串聯、聯繫、在理念上有所溝通的組織,這次在危機狀況下,就立即聚集起來討論該怎麼辦。
因為他們發現,街頭上的人很快地生活就陷入了困境。因為他們完全失去了平常會來發的物資──沒有人敢再去發物資;有些地方甚至因為怕病毒傳播,把廁所或飲水機全部都封起來,他們失去了這些民生上的必需品。工作上也是完全停掉,工地的工作機會、舉海報的工作機會都完全沒了。這時候其實很需要外界的幫助,可是大家都怕得要死,五月中時,大家都覺得那是高風險地區。
可是就有兩三個團體馬上聚集起來,後來便很有規律的發放物資。同時透過作家、名人的管道向外界募資,幕到大量物資後,也有艋舺在地商家願意騰出空間來擺放。整個進行過程中,民間社會的韌性是非常足夠的,可以看到他們的反應非常迅速、有條理,也讓街頭上幾百個無家者的必要生計得到保障。我覺得這方面特別能看出台灣社會進步之處。前面提到那些針對無家者的污名,後來我也有看到一些其他的媒體,直接去採訪無家者、服務無家者的團體,糾正這些錯誤的報導。臺灣社會在這方面,這幾年來的進步非常的大。特別是從此次疫情中可以看出來。
【本集節目是由臺灣社會學刊製作播出的《作伙來想社會》】
開啟小鈴鐺、按下追蹤,持續關注最新節目
「作伙來想社會」是什麼?
「作伙來想社會」是由《臺灣社會學刊》製作的一系列社會學科普短片與廣播,透過邀請學術論文的作者現身說法,用平易近人的語言,希望將臺灣社會學界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帶給所有社會大眾。本計劃受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中心「補助學術期刊數位傳播」方案、臺灣社會學會經費補助。
更多資訊:
臺灣社會學會粉絲專頁|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wsociology
本集底本論文全文 |https://reurl.cc/r1L7Gk
片尾配樂|DJ綠川